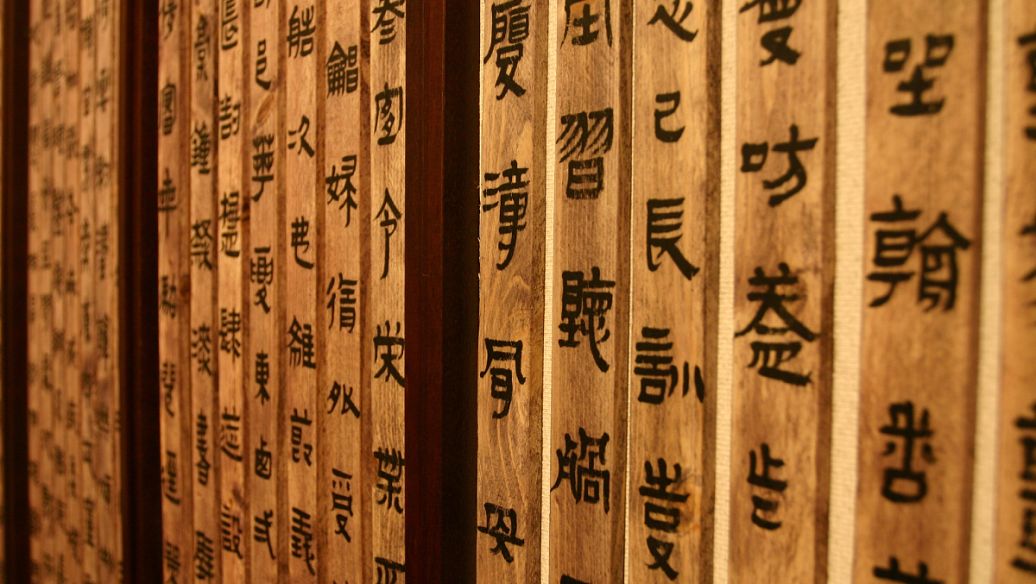或曰:「管仲儉乎?」曰:「管氏有三歸,官事不攝,焉得儉?」
【考異】皇本「儉」下有「乎」字。
【考證】過庭録:凡論語言或者,大抵老氏之徒。如或曰「以德報怨」,卽老子『報怨以德」也。管子爲道家之言先於老子。老子治天下有三寶,其一曰儉。又老子言禮,此以管仲爲儉爲知禮,皆道家之說。 論語後録。韓非子:「管仲相齊,曰:『臣貴矣,然而臣貧。』桓公曰:『使子有三歸之家。』曰:「臣富矣,然而臣卑。』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。曰:『臣尊矣,然而臣疏。』乃立爲仲父。孔子聞而非之曰:「泰侈偪上。」」一曰:「管仲父出,朱蓋青衣,置鼓而歸,庭有陳鼎,家有三歸。孔子曰:『良大夫也。其侈偪上。』」說苑:「齊桓公立仲父,致大夫曰:『善我者入門而右,不善我者入門而左。』有中門而立者,桓公問焉。曰:『管仲之智可與謀天下,其强可與取天下,君恃其信乎,內政委焉,外政斷焉,民而歸之,是亦可奪也。』桓公曰:『善。』乃謂管仲:『政則卒歸於子矣,政之所不及,惟子是匡。』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。」案兩書之說不合。 四書摭餘說。黄氏日抄云:「說苑謂管仲避得民而作三歸,殆于蕭何田宅自汙之類。想大爲之臺,故云非儉,而臺以處三歸之婦人,故以爲名歟?」至筭家三歸法之說似陋,歸三路人心之說似鑿,都不必從。 秋槎雜記:春秋莊十九年經:「公子结媵陳人之婦于鄄。」左氏無傳。公羊云:「媵者何?諸侯娶一國,則二國往媵之,以姪娣從。姪者何?兄之子也。娣者何?弟也。諸侯一聘九女,諸侯不再娶。」成十年經:「齊人來媵。」公羊傳云:「三國來媵,非禮也。惟天子取十二女。」左氏成八年經,杜注:「古者諸侯娶適夫人及左右媵乃有姪娣,皆同姓之國。國三人,凡九女。」穀梁注全錄杜注,則是三傳意皆以天子諸侯娶妻班次有三。適也,娣乜,姪也。天子取后,三國媵之,國三人,並后本國爲十二女。諸侯娶夫人,二國媵之,並夫人本國爲九女。夫人本國之媵,從夫人歸于夫家者也。士昏禮:「女從者畢袗玄。」又云「媵布席于奥」,鄭注「女從者,謂姪娣也。媵,謂女從者也」是也。二國之媵或與夫人同行,春秋成八年「夏,宋公使公孫壽來纳幣。冬,衛人來媵。九年春二月,伯姬歸于宋」是也。或後夫人行,「九年夏,晉人來媵。十年夏,齊人來媵」是也。其本國歸女爲一次,二國各一次,故曰三歸。左氏譏齊媵爲異姓,公羊譏齊媵爲三國媵天子,皆不譏齊媵女之遲也。包曰「三姓女」,依左氏成八年傳「同姓媵之,異姓則否」,包說非也。鮑曰:「三娶女。國君娶夫人,大夫娶妻,姪娣不言娶,故公羊云諸侯不再娶。」鮑說亦非也。又案曲禮「大夫不名世臣姪娣,士不名家相長妾」,正義引熊氏云:「士有一妻二妾。言長妾者當謂娣。」是大夫姪娣俱不名,士但不名娣,異于大夫,其皆有姪娣明矣。士無娣則媵二姪,士昏禮「雖無娣媵先」是也。故詩江有汜序正義據士昏禮以爲士有姪娣,但不必備。據喪大記「大夫撫姪娣」,以爲大夫有姪娣而未明言。大夫士姪娣之數,以諸侯八妾士二妾例之,卿當六妾,大夫當四妾。北齊元孝友傳:「孝友嘗奏表曰:『古諸侯娶九女,士一妻一妾。晉令诸侯王置妾八人,郡君侯妾六人,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,第三第四有三妾,第五第六有二妾,第七第八有一妾,蓋仿古制而變通之。』」 論語稽求篇。舊注引包咸說。謂三歸是娶三姓女,婦人謂嫁爲歸。諸儒說皆如此。朱注獨謂三歸是臺名,引劉向說苑爲據。則遍考諸書,並無管仲築臺之事。卽諸書所引仲事,亦並無有以三歸爲臺名之說,劉向誤述也。或謂三歸臺亦是因三娶而築臺以名之,古凡娶女多築臺,如詩衛宣公築新臺娶齊女,左傳魯莊公築臺臨黨氏娶孟任類,然管氏築臺終無據,不可爲訓。 孫志祖讀書脞録:三歸之爲臺名是也。然所以名三歸者,亦以娶三姓女之故。如詩衛宣公築新臺於河上以要齊女,左傳魯莊公築臺臨黨氏以娶孟任之類。
【集解】包曰:「或人見孔子小之,以爲謂之大儉乎。三歸者,取三姓女也。婦人謂嫁曰歸。攝,猶兼也。禮,國君事大,官各有人,大夫兼并。今管仲家臣備職,非爲儉也。」
【唐以前古注】皇疏:禮,諸侯一娶三國九女,以一大國爲正夫人,正夫人之兄弟女一人,又夫人之妹一人,謂之姪娣,隨夫人來爲妾。又二小國之女來爲媵,媵亦有姪娣自隨。既每國三人,三國故九人也。大夫婚不越境,但一國娶三女,以一爲正室,二人姪娣從爲妾也。管仲是齊大夫,而一娶三國九人,故云有三歸也。
【集注】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。三歸,臺名。事見説苑。攝,兼也。家臣不能具官,一人常兼數事,管仲不然,皆言其侈。
别解一梁玉繩瞥記:三歸,注疏及史記禮書、漢書地理志、戰國策周策皆以爲三姓女,惟朱子從說苑以爲臺名。翟灝以管氏本書輕重篇證之,三歸特一地名,蓋其地以歸之不歸而名之也。本公家地,桓公賜以爲采邑耳。按晏子春秋雜下篇:「晏子相景公,老,辭邑。公曰:『先君桓公有管仲,身老,賞之以三歸,澤及子孫。今欲爲夫子三歸,澤及子孫,豈不可哉?』」又韓子外儲右下及難二。「管仲相齊,曰:『臣貴矣,然而臣貧。』桓公曰:『使子有三歸之家。』據此,則爲地名者近之。史記公孫弘曰:「管仲相齊有三歸,侈擬於君。」亦是言其侈富也。
按:此以三歸爲地名。劉寶楠云:「管子明言五衢之名,樹下談語,專務淫游,終日不歸。歸是民歸其居,豈得爲管仲所有,而遂附會爲地名耶?」則地名之說非也。
【別解二】羣經平議。就婦人言之謂之歸,自管仲言之當謂之娶,乃諸書多言三歸,無言三娶者。且如其説,亦是不知禮之事,而非不儉之事。則其說非也。朱注據說苑「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」,故以三歸爲臺名。然管仲築臺之事不見於他書。戰國策周策曰:「宋君奪民時以爲臺,而民非之,無忠臣以掩蓋之也。子罕釋相爲司空,民非子罕而善其君。齊桓公宫中七市,女閭七百,國人非之。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,非自傷于民也。」說苑所謂「自傷於民」者疑卽本此。涉上文子罕事而誤爲築臺耳。古事若此者往往有之。未足據也。然則三歸當作何解?韓非子外储說篇曰:「管仲相齊,曰:『臣貴矣,然而臣貧。』桓公曰:『使子有三歸之家。』一曰管仲父出,朱蓋青衣,置鼓而歸,庭有陳鼎,家有三歸。」韓非子先秦古書,足可依據。先云「置鼓而歸」,後云「家有三歸」,是所謂歸者,卽以管仲言,謂管仲自朝而歸。其家有三處也。家有三處,則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從可知矣。故足見其奢。且美女之充下陳者亦必三處如一,故足爲女閭七百分謗,而娶三姓之說亦或從此出也。晏子春秋雜篇曰:「惜吾先君桓公有管仲,恤勞齊國,身老。賞之以三歸,澤及子孫。」是又以三歸爲桓公所賜,蓋猶漢世賜甲第一區之比。賞之以三歸,猶云賞之以甲第三區耳。故因晏子辭邑而景公舉此事以止之也。其賞之在身老之後,則娶三姓女之說可知其非矣。近人或因此謂三歸是邑名,則又不然。若是邑名,不得云「使子有三歸之家」,亦不得云「家有三歸」也。合諸書參之,三歸之義可見。下云「官事不攝」,亦卽承此而言。管仲家有三處,一處有一處之官,不相兼攝,是謂官事不攝。但謂家臣具官,猶未見其奢矣。
按:此以三歸爲家有三處,較舊注、朱注義均長,似可從。
别解三包慎言溫故録:韓非子:「管仲相齊,曰:『臣貴矣,然而臣貧。』桓公曰:「使子有三歸之家。」孔子聞之曰,『泰侈逼上。』漢書公孫弘傳:「管仲相桓公有三歸,侈擬於君。」禮樂志:「陪臣管仲、季氏三歸雍徹,八佾舞庭。」由此數文推之,三歸當爲僭侈之事。古「歸」與「饋」通。公羊注引逸禮云:「天子四祭四薦,諸侯三祭三薦,大夫士再祭再薦。」又云:「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,天子元士、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,諸侯之士特豕。」然則三歸云者,其以三牲獻與?故班氏與季氏之舞佾歌雍同稱。晏子春秋內篇:「公曰:『昔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功,邑狐與穀,以共宗廟之鮮,賜其忠臣。今子忠臣也,寡人請賜子州。』辭曰:『管子有一美,嬰不如也,有一惡,嬰弗忍爲也。」其宗廟養鲜,終辭而不受。」外篇又云:「晏子老,辭邑。公曰:『桓公與管仲狐與穀以爲賞邑。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,恤劳齊國,身老,賞之以三歸,澤及子孫。今夫子亦相寡人,欲爲夫子三歸,澤及子孫。』」合觀內、外篇所云,則三歸亦出於桓公所賜。內篇言以共宗廟之鲜,而外篇言賞以三歸,則三歸爲以三牲獻無疑。晏子以三歸爲管仲之一惡,亦謂其侈擬於君。
按:此以三歸爲三牲,「歸」與「饋」通,義稍迂曲。
别解四武億羣經義證:臺爲府庫之屬,古以藏泉布。史記周本紀:「散鹿臺之泉。」管子三至篇:「請散棧臺之錢,散諸城陽。鹿臺之布,散諸濟陰。」是齊舊有二臺,以爲貯藏之所。韓非子「管仲相齊」云云,以三歸對貧言,則歸臺卽府庫别名矣。泉志載布文有「齊歸化」三字,疑爲三歸所斂之貨。又晏子春秋內篇云:「管仲恤勞齊國,身老,賞之以三歸,泽及子孫。」又一證也。論語發微:三歸,臺名,古藏貨財之所。聚斂卽是不儉,若取三姓女,則桓公安得賞之? 黃氏後案:國策周策。「齊桓公宫中七市,女閭七百,國人非之。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。非自傷於民也。」包注據之。説苑善説篇:「桓公疑政歸管仲,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。」朱子注據之。家東發先生曰:「臺以處三歸之婦人,故名。」杭堇浦云:「古昏禮有築臺以迎女之事。詩衛宣公築新臺娶齊女,左傳魯莊公築臺臨黨氏娶孟任。」是合二注爲一事也。武虚谷曰:「臺爲府庫之屬,古以藏泉布。史記周本紀『散鹿臺之泉』,說文解字通論『武王散鹿臺之錢』是也。管子三至篇:「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,鹿臺之布散諸濟陰。」是齊國舊有二臺以爲貯藏之所也。韓非子管仲相齊,曰:『臣貴矣,然而臣貧。』桓公曰:「使子有三歸之家。』晏子春秋:「管仲恤勞齊國,身老,賞之以三歸,澤及子孫。」皆其據也。」
按:此以三歸爲藏貨財之所,最爲有力,卽論語稽亦取之。宦伯銘謂?「周策本文無取三歸之說,鲍注以上文女閭云云,遂謂取女以掩,因以婦人謂嫁曰歸附會之。然諸侯得取三國女,仲果取三國女,是與塞門反坫同,非僅不儉也。且取三國女,而晏子春秋曷言賞也?又以歸三不歸爲采地,則采地無傷於儉也。今以韓非子『得三歸而富之』語觀之,正與儉字對勘。其云『三歸之家』者,猶云千乘之家也。」亦可備一說。